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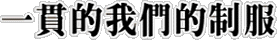
 政治大學沒有規定制服,不過政大人似乎有穿制服的習慣。從風雨走
廊往下走時穿著系服班服人的不可計數,即使該服裝設計的說有多難
看多沒設計概念,多麼適合在各種觀視角度傷害人類的視覺;或是說
班上有個女生因為「莊大衛」零號設計師導致髮型全毀,在全班一致
的訕笑後,還是又有許多女生去接受那位零號設計師的蹂躪。 政治大學沒有規定制服,不過政大人似乎有穿制服的習慣。從風雨走
廊往下走時穿著系服班服人的不可計數,即使該服裝設計的說有多難
看多沒設計概念,多麼適合在各種觀視角度傷害人類的視覺;或是說
班上有個女生因為「莊大衛」零號設計師導致髮型全毀,在全班一致
的訕笑後,還是又有許多女生去接受那位零號設計師的蹂躪。
 當然政大人的統一制服不是班服系服、政大員生合作社推出的愛校 T
恤,或是老教授都喜歡的那種印有政大校徽的白色運動薄外套。政大
人所穿著的,是在一種觀視的角度、或是其他不想失去的事物,在失
去時重新關心重視注意我們一貫視若草芥的一切,在失去之後一陣惱
怒懊悔悲傷,然後不久後回到政大人一貫的自利冷漠與健忘。 當然政大人的統一制服不是班服系服、政大員生合作社推出的愛校 T
恤,或是老教授都喜歡的那種印有政大校徽的白色運動薄外套。政大
人所穿著的,是在一種觀視的角度、或是其他不想失去的事物,在失
去時重新關心重視注意我們一貫視若草芥的一切,在失去之後一陣惱
怒懊悔悲傷,然後不久後回到政大人一貫的自利冷漠與健忘。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八日開始,政大人又開始這個政大人的冷漠制服
迴圈。約莫五六十位政大新聞系(包括大學部和碩士班)廣電系師生
看了前幾天的商業電視台新聞,集結在立法院前抗議公共電視廢台,
之後這群人在二十一日晚上去放天燈、二十二日早上又去立院門前守
候,幾天來大字報呼口號,好不熱鬧。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八日開始,政大人又開始這個政大人的冷漠制服
迴圈。約莫五六十位政大新聞系(包括大學部和碩士班)廣電系師生
看了前幾天的商業電視台新聞,集結在立法院前抗議公共電視廢台,
之後這群人在二十一日晚上去放天燈、二十二日早上又去立院門前守
候,幾天來大字報呼口號,好不熱鬧。
 這五六十位不知道有多少是去抗議多少是去看熱鬧。不過所有的商業
電台拍攝採訪的都是抗議的,沒有哪個看熱鬧的上了電視;換句話說
,這不是在我們的觀視角度內。 這五六十位不知道有多少是去抗議多少是去看熱鬧。不過所有的商業
電台拍攝採訪的都是抗議的,沒有哪個看熱鬧的上了電視;換句話說
,這不是在我們的觀視角度內。
 抗議的是什麼呢?抗議的是我們以一貫冷漠方式閱讀死記的傳院教科
書陳腔濫調,我們在新聞學、大眾傳播與媒介、新聞史、廣電概論中
的空虛理想,如何的在我們一貫冷漠對待的台灣政治手中失去。抗議
我們要失去, 那些我們在抗議前夕才去溫習的 NHK、BBC、PBS 等等
不屬於我們語文的名詞,在抗議之後我們繼續回家開開心打開商業電
台,繼續看陽帆余天超級星期天。 抗議的是什麼呢?抗議的是我們以一貫冷漠方式閱讀死記的傳院教科
書陳腔濫調,我們在新聞學、大眾傳播與媒介、新聞史、廣電概論中
的空虛理想,如何的在我們一貫冷漠對待的台灣政治手中失去。抗議
我們要失去, 那些我們在抗議前夕才去溫習的 NHK、BBC、PBS 等等
不屬於我們語文的名詞,在抗議之後我們繼續回家開開心打開商業電
台,繼續看陽帆余天超級星期天。
 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後,行政大樓八十輛學生汽車的喇叭聲在時
間潮來潮往後消逝於無形,關於喇叭聲的記憶我們也不清楚還是否存
在。總之,我們失去了學生在校園裡的停車位,有些人是說失去了校
園民主、失去學生的平等參與,或是,呃,尊嚴;在失去時我們繫上
紅絲帶高明喇叭用口語用電子布告欄憤怒咒罵董保城李登科,然後我
們便開始失憶,廢除三一後門條款口號僅適合在代聯會長競選的一週
內讓我們短暫溫習。 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後,行政大樓八十輛學生汽車的喇叭聲在時
間潮來潮往後消逝於無形,關於喇叭聲的記憶我們也不清楚還是否存
在。總之,我們失去了學生在校園裡的停車位,有些人是說失去了校
園民主、失去學生的平等參與,或是,呃,尊嚴;在失去時我們繫上
紅絲帶高明喇叭用口語用電子布告欄憤怒咒罵董保城李登科,然後我
們便開始失憶,廢除三一後門條款口號僅適合在代聯會長競選的一週
內讓我們短暫溫習。
 我們失憶的內容包括地政系有個老師叫做李永展,他所提的政大汽機
車長期停放方案如何因為我們的冷漠而逐漸湮滅飄散;而一個推動政
大校園景觀改造、推動汽機車停放方案,名為綠潮的那個社團,激情
的我們也在披回制服之後,不知何時何地如何的失去了那個社團,還
有那個社團以熱情觀看政大校園景觀的那個角度。 我們失憶的內容包括地政系有個老師叫做李永展,他所提的政大汽機
車長期停放方案如何因為我們的冷漠而逐漸湮滅飄散;而一個推動政
大校園景觀改造、推動汽機車停放方案,名為綠潮的那個社團,激情
的我們也在披回制服之後,不知何時何地如何的失去了那個社團,還
有那個社團以熱情觀看政大校園景觀的那個角度。
 我們有無數個制服迴圈,我們在一個停電的端午節失去我們儲存在網
路上某個硬碟的所有共同記憶,我們抗議、我們投書、我們找立法委
員質詢,然後大家還是遺忘了那個站,上貓空行館,任「醉夢溪畔」
成為心理諮商中心的筆記書以及泡沫紅茶坊的名字。我們有幾位社會
系的同學曾經誓言「今晚我們聚在一起,一同為我們的理想而拼鬥」
,抗議收取學分費,過了半年,為理想而拼鬥的他們還是乖乖繳了學
分費。 我們有無數個制服迴圈,我們在一個停電的端午節失去我們儲存在網
路上某個硬碟的所有共同記憶,我們抗議、我們投書、我們找立法委
員質詢,然後大家還是遺忘了那個站,上貓空行館,任「醉夢溪畔」
成為心理諮商中心的筆記書以及泡沫紅茶坊的名字。我們有幾位社會
系的同學曾經誓言「今晚我們聚在一起,一同為我們的理想而拼鬥」
,抗議收取學分費,過了半年,為理想而拼鬥的他們還是乖乖繳了學
分費。
 我們忘了,我們真的忘了。忘記了我們的每一次失去,每一次痛苦每
一次錯愕每一次的抗議;然後,是我們的再一次失去,再一次痛苦再
一次錯愕再一次的抗議,再一件的制服。 我們忘了,我們真的忘了。忘記了我們的每一次失去,每一次痛苦每
一次錯愕每一次的抗議;然後,是我們的再一次失去,再一次痛苦再
一次錯愕再一次的抗議,再一件的制服。
 制服是好的,制服讓我們如此輕易的辨識彼此,知道彼此並不孤獨。
所以我們已經步入沒有制服的大學校園,褪下了卡其服,但是卻從未
褪下我們真正的制服。偶而,我們在失去一些觀視角度的時候心悸亢
奮,亢奮中再添上一件制服,再執行一次迴圈。穿了再多件的制服我
們也沒有私毫不適,因為我們自始至終,就是一貫的,冷漠。 制服是好的,制服讓我們如此輕易的辨識彼此,知道彼此並不孤獨。
所以我們已經步入沒有制服的大學校園,褪下了卡其服,但是卻從未
褪下我們真正的制服。偶而,我們在失去一些觀視角度的時候心悸亢
奮,亢奮中再添上一件制服,再執行一次迴圈。穿了再多件的制服我
們也沒有私毫不適,因為我們自始至終,就是一貫的,冷漠。
 十八日抗議會場上有位長的有點像日本知名摔角手安生洋二的聾人朋
友,拿著面牌子,說:「公視,讓聾人聽見自己」。讓聾人聽見自己
?好像極富哲理,不懂,制服冷漠也讓我們不想懂。 十八日抗議會場上有位長的有點像日本知名摔角手安生洋二的聾人朋
友,拿著面牌子,說:「公視,讓聾人聽見自己」。讓聾人聽見自己
?好像極富哲理,不懂,制服冷漠也讓我們不想懂。
 我們的冷漠也不想懂,這位與音樂、朗誦、歌謠、頌詠絕緣的朋友,
怎樣捍衛他失去的觀視角度。 我們的冷漠也不想懂,這位與音樂、朗誦、歌謠、頌詠絕緣的朋友,
怎樣捍衛他失去的觀視角度。
 我們也不在乎,今天、明天、後天,所失去的每一種觀視角度。 我們也不在乎,今天、明天、後天,所失去的每一種觀視角度。
|